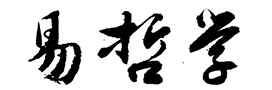一、引言
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流行一种“信息不对称”学说。指的是系统中的某一方拥有比另一方更广泛的信息获取,就会在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中获取本质性的优势。此学说就表象而论没有任何理论瑕疵,但就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却不去认真追究,抑或追究也将之归结为智商或知识结构。
其实,同样境遇的社会个体间是不存在所谓“信息不对称”的。正如同散户在与外部隔绝的前提下在交易大厅中面对一片交易数据,他们的信息是“绝对对称”的。而之所以出现“不对称”,是因为给个体的操盘手下发指令的“场外主体”占据在什么层级的信息平台上。
这就说明,所谓“信息不对称”学说,其实是将本质上属于超越与被超越地位的“两行论”理论视域中的逻辑现实强行置于“一行论”的论域生硬地派生出来的“现象理论”。直观地说,“两行论”的逻辑视域是一个类似海绵网状结构的立体叠合逻辑视域,而“一行论”则是一个平面视域。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带有逻辑视域发生、成长、完善属性的立体化无限延伸的“两行论”逻辑视域,而后胡塞尔的现象学,特别是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的所谓现象学理论,如“社会交往理论”、“个体经济人假设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所谓“信息不对称理论”,都是刻意褫夺本质性的逻辑真相而着意进行“现象学呈显”的纯粹“唯象理论”。
现象学是强调本质还原的,而无本质究问的“唯象理论”充其量是绘画式的事实表达。而需要我们倍加警觉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也已清晰完成了的对社会和经济的“个体-社会”关系的两行表达,每每遇到与现代“唯象理论”“被对话”的局面,而且不难设想,“被对话”的结局无一例外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被否定、被超越、被解构、被创造。由此,两行论的正本清源极为必要。
二、超越与被超越的逻辑时间判定
从现实的视角看,两行逻辑论是派生于两行系统论的。虽然逻辑本质上属于人类思维的内生构造,是抽象的一致性原则下的叠磊派生,但其原始的构成质素和形式化的视域生成原则却基于现实的感性直观。更为关键的是,逻辑的结构和系统的结构生成都受一关键制约——时间。这个时间不一定是自然时间,但它是记录叠磊生成次序的时间,只要有次序,就必然有标志前后顺序的时间。胡塞尔称其为内在的现象学时间。在所有的理论体系中,只有形而上学的分析体系标榜消灭了时间,那是因为在形而上学的分析逻辑学家看来,推理的一致性决定了任一逻辑起点到任一逻辑终点的推理次序之间是绝对等价从而是可以逻辑互换的。既然绝对等价,就无需强调逻辑次序,因而也就没有逻辑时间。但哥德尔定理否定了形而上学的这一根本前提。胡塞尔意义上的逻辑生成本质上就包括了一个可逻辑互换的的分析视域向不可逻辑互换的超越性逻辑视域的叠磊生成过程,指出这是我们人类逻辑理性展开的普遍模式。
可见,超越性是与逻辑的内在时间紧密关联的。正像在自然时间系统中今天的当下不可超越自身而对明天的事实给出精确地判断,在逻辑时间或现象学时间系统中,时间节点之前的逻辑视域不能包含时间节点之后逻辑视域。这个节点构成超越与被超越的标志。
以此纵观所谓超越性,本质上是逻辑视域的封闭性与扩展性之间的关系。当一个固定逻辑视域下的逻辑学家不明白扩展的、超越的逻辑视域的生成法则时,他一定被置于超越体系视域下被超越的地位。这如同小学生之于线性代数、中学生之于高等分析,虽然有“奥数”题目之类,这些都本质上是超越逻辑系统中的命题但低级逻辑系统亦可参透的逻辑灰色地带。但实质上中学生是不胜任高等数学分析的逻辑运思的,在“数学等级”这个“现象学时间节点”面前,高等数学超越了初等数学,初等数学体系化地被置于逻辑上的“被超越”地位。
三、“两行论”视域下的“不对称”现实和“原始反终”的“道术”追求
逻辑视域的止于封闭,在《荀子》那里称之为“所蔽”,而自我超越的过程称之为“解蔽”。“所蔽”与“解蔽”之间,天然形成一“两行论”的逻辑张力结构,超越与被超越的“不对称性”历然凸显。
“解蔽”是中国哲学的一项恒久的事业。它始自于自然意义上的“见世面”领域的开阔,逐渐哲学提升至超越时间限止的“道术”。《管子》曰: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知配也。《形势》
管子的“道术”体系基本不离开礼乐制度下的层级现实社会,“两行观”建立在“家-乡”、“乡-国”、“国-天下”、“万物-天”的不同层级之下。即管子现实关注真实的“两行系统社会”。上下行之间的“解蔽”与“所蔽”的超越与被超越关系井然陈列。不同层级有不同层级之“道”,显然,超越性表现在不同层次下的“道”,超越了它的下行而被超越于它的上行。其暗示的逻辑是“道”的晋级路径与你的现实视域的扩大紧密合一。
在“易道”中,“道”突破了现实两行系统社会的视域止限,变成针对“时间”穿透的理论操作。所谓“原始反终”就是打通“始”与“终”之间的逻辑阻隔,让逻辑的超越成为可能。现实的路径是,将自然世界的衍化样态抽象成普适化、一般化的“成物之理”,以“理”的逻辑不得不然性贯穿始终,实现“道术”的超越。当然,中国哲学的“道术”超越谋求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谋求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西方形而上学在存在论意义上谋求终极的“一网打尽”,即在逻辑面前的一切都彻底澄明。但中国哲学似乎有人类自知之明,明天人之分,更清晰于“道术”的晋级穷无止境。用现代逻辑理性看来,中国哲学反而不会陷入哥德尔定理式的逻辑陷阱,却与胡塞尔的超越逻辑世界契合。换言之,中国哲学的两行论更集中关注于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
四、“诚”“成”互训展开的人文道术及其人文正当性之所由
“道术”以“成物之理”之“成”转化为道术原则之“诚”,在本然之理与应然之则之间建立起一座“正当性”原则所出的桥梁。这种正当性瞄准的靶的正是如何处置两行之间不对称性这一逻辑事实。
中国哲学的絜矩之道针对的是“君子”。所谓“君子”在两行关系中的本质属性就是“超越者”,就是相对于“被超越者”之“所蔽”处境几乎具有宰制地位优势的“解蔽者”。“超越者”的地位一旦被获取,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理路:一个是按照“超越者”自身的“成己”秉性,这将把“超越”“解蔽”的优势发展得淋漓尽致,一如西方的资本集团,一旦获得资本对社会的宰制地位,资本就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成己”路径全速前行。这时,处于下行地位的任何个体的任何“解蔽自身”和“超越地位”谋求,都将被资本视作异己之物本能地加以打压,换言之,“信息的对称性”正是资本社会绝对不能容许存在的“被消灭对象”。有意思的是,关于资本运作的“经济学”却把“信息对称性”这个被资本追杀的幽灵当成理论奠基。“超越者”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是指向社会命运共同体综合的“成物之理”,这就要求上行超越者放弃自身集团的“成己”谋求而代之以对“两行命运综合体”的“成物”谋求。这就涉及三个基本的理论要素:其一是“下行命运体”的“成己之理”如何对待处置,其二是“上行命运体”的“成己之理”如何对待处置,其三是在“两行命运体综合成物之理”的谋求下,上下行的关系如何处置。
只有明确了上述有关上下行“不对称”地位的本质,并明确上行衍化路径的本质分野,才能明确中国哲学的主体和任务。中国哲学的全部而不是分支流派,都是在第二条道路所指的方向上理论界定遍及三个理论要素的正当合法性。其逻辑前提是,共命运体的综合成物之理的满足是正当合法性的由来。
“下行社会”由于其固有的“所蔽”及其“被超越”地位,自身的“成己之理”最难得到满足。而所谓下行社会又是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单元。在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前提下,上行社会只要不是僭越于共同体之外的异类,就只能成为共同体利益的如实代表。那么它必须以共同体的“成物之理”为依据成为两行社会的管理者。这就使得满足“下行社会”个体的“成己之理”的要求成为理论先决,而它与共同体的“成物之理”息息相关。至于“上行结构”自身,由于其具有维护“成己之理”的本能,从来都是中国哲学约束和限止的对象。
上下行本身及其两行关系之间有如上三个层次的“成物之理”,那么这个“成”就成为“理”的保障。换言之,逻辑地说,有按照“成物之理”要求的所“成”,就本然地(不一定必然)保证所成之物符合于“理”。以“成”为道之统,就能够在本然的逻辑说理范畴内实现“成”之“始”与“理”之“终”之间的逻辑统一。即在本然逻辑范畴内实现“原始反终”的时间穿透,而实现“道通一贯”。
“理者,成物之文也”,
“道者,万物之所成,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
当“道术”完成了上述意义的理论成熟,那么人文之道的奠基也就自然而然派生出来,当把本然之“成”置换成应然之“诚”并植入“君子”的内心之后,“诚”就会贯通地兑现“成”,如实地遵循“两行成物之理”,将“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旗帜高扬起来。
回到不对称性上来,以“诚”为人文之质的道术贯彻,不是旨在消除两行关系的不对称性,而是因应这种不对称性进行“上行”共同体的综合擘画,使得下行的构成充当资源得以满足整体最优化目标下的资源配置,在满足不同层面“成物之理”的原则下,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系统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