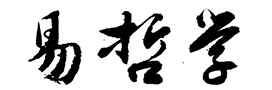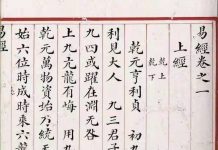《周易》是一本书,但又不是普通的书。就其实质来说,它是承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的思想脐带。在它成书之前(这里指的是“经”而非“传”),即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演替到殷商之末,中华文明大体具有这样的特征:成熟的渔猎文明与破碎化的农耕文明相混、巫祝文化与部落文化相杂、社会的组织行为高度依赖祭祀与兵戎、天人之际密而未分、人与自然浑然如一。其现代性特质是,1.人类从自然生态链中并未完全脱身而出,物种的种系特征强于人类特征:渔猎文明的本质在于“人”作为能量强大的物种能够置其他动物于被宰制的地位,而破碎化的农耕文明仅只说明人类掌握了培植农作物的技术,补充性地获得有限食物;2.人群间的行为模式遵循不得不然的自然规律,并将这种纯粹的自然规律看成是天人系统总体规律的一部分:部落文化的衍化遵循着高度的原始同一性,从母系社会到部落间对偶婚姻再到酋长制,反映着的是自然的衍化规律而非人文的擘画规律,而原始的巫祝文化,在思维范式上的预定假设就是包括人在内的全部自然都属于一个天人共一的统一共命运体,人类作为共命运体当中的个化命运体,只能受到共命运体规律的绝对支配,“巫祝”活动是针对着“规律失常”的警示和通过“通神明”的间接干预;3.社会化活动表现为不得不然的应急,即社会组织化的动力和目的在于生存维系本身及其天人共同体成员身份的确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天人共同体(包括逝去的祖先)成员身份的确认,因而有氏族、祖宗、社会(集会于社),祭祀仪式是社会(血缘)组织维系的第一动力,而“戎”则是在集体安全层面首要的生存条件,其使命在于“卫”,即捍卫集团共同体的生存权利,由“卫”生成的社会组织化,作为集体生存的必须,当然责无旁贷;4.由于人们将自身泥于自然本身,带有人文色彩的“我是谁”、“我从哪来”、“要到哪去”的觉醒意识便初蒙未开。虽然孔子儒家将三代之礼人文一同,并进而上推到三皇五帝,以损益消长连贯之,但这却不是事实。以“德”为核心的自觉人文意识,并不产生于殷商之前,而产生于殷周嬗递之后。其核心标志,就是殷商之前,天人之际密而未分、人与自然浑然如一。
有周的人文革命,画出了一条划时代的际界,本质上呼唤出这样一个时代:人类如何从自然的必然世界走出?也就是说,人如何别于自然、别于禽兽,向着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发问求解。这标志着哲学的真正开启。
周人将自己精神上的祖先定位为后稷,预示着周人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先进性在于能够实现农耕文明。与破碎化的农耕文明骤然相别,周人设计中的农耕文明是社会化的即社会全员生产力总动员的农耕文明。它的深刻意义在于:仰赖农耕文明的社会产出,人类能够自足地实现整体化的生存所需。这意味着人类将自身生存的命运从自然的从动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把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性。因而,周人甫一取代殷人获得天下,便以“井田制”为基础环节,设计出以农为本的、社会全员生产力广泛参与的、集体化“现代工业管理模式”下的农耕文明体系:“井田”有似一线的生产车间,以井田制为组织形式的耕农有似车间小组,若干井田为一个高级组织单元,若干高级组织单元构成更高级的组织单元,他们接受由上而下称之为“司农”的官僚体系的垂直领导,以质量效益为目标加以管理与服务。从而,“农作”超越了“培植技术”这一人对自然界主观改造的可能性,一跃成为人类对自我生存方式可自主安排的战略主动:人类的未来生存样态直观可期、全员就业全员享受的生产成果可期;进而,围绕着生产革命展开的人类自身生活样态不但可期,而且可以精神化升华。简言之,人类获得了从自然界必然地位中走出,进入一个不能用自然规律表达的新的人类文明世界的理论前提。
由此,周人在文化上展现出来的现代特征,充满了对人类对即将获得的超越自然地位的礼赞、憧憬和设计。1.充分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人类在生理属性上别于自然、别于禽兽。那么,人类在文化上别于禽兽的规定性在哪里?即,人类的根本意义和根本地位在哪里?由此,“人类”这一别自然的格属赫然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生命样态清晰呈现。在这个总纲之下,超越自然、超越禽兽的“人类共同体”的目的、意义及其行为规范,被以人的意志设计而出,不但不受自然规律的规制禁锢,而且大有“命运在我”的人文观。2.重新界定天人关系。“天地处焉”“四时行焉”,天本无意志,但人文世界展现人类意志,由此“天”也就伴生了“人文意志”:“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意志、整体诉求、整体命运,就变成了“天”的意志、诉求甚或命运。“天”既是人类的主宰系统,又是人类的辅助系统。“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获得了高度的理论协调。3.人类间的交往方式要别自然、别禽兽。人类给人类自身立宪,在殷周之际有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人文规则的独立化和超越化。别自然,别禽兽是以反省的方式以动物世界为镜鉴,规划人类的行为方式。于是,“郁郁乎文”“彬彬而礼”的礼乐文明纲领以高尚的自我理想设计的方式被庄严提出,究问每一种人类行为的“人文意义”而成“礼”。注意之前的“礼”是着眼于“天人关系”的,而今着眼的是“人类行为与人文意义之间的关系”即人类伦理关系。4.人类的组织方式展现为四个维度:由狭义的血缘伦理共同体组成的以“祖-祢”亲疏秩序为属性的狭隘“社会”;由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产-管理方式为维度的生产组织即“营”;由“什伍制”组织起来的安全保卫体系即“卫”;以抽象的“人文意义”规定而成的尊卑秩序。前者为血缘伦理,简为“亲亲”;后者为社会伦理,简称“尊尊”。中间两项“营”“卫”是社会命运有机体之“成物之理”所本然规定,是自然之理在人文世界的本质残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5.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诸元也是不同形式的命运体,譬如个人就是最基础的命运体单元;而大于二人组成的单元如家庭、家族、乡里、行伍、侯国乃至所谓天下,也都是不同级别的命运体。它们互相嵌套,构成不同的“两行组织结构”,最高者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诸元既为命运体(共命运体也是命运体),就有各自的“成物之理”,一般地,两行命运体的上行与下行命运体有各自独立的“成物之理”,两个“成物之理”之间的交互关系才是两行命运体间的本质关系。不失一般性,周秦之际的中国哲学其理论焦点就在于两行成物之理之间的交互关系,即两行关系。该关系学说称之为“两行论”。
《周易》就是在上述社会、思想革命之际形成的书。有关《周易》的哲学讨论,离不开上述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