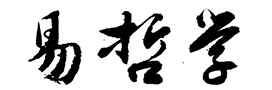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论冯友兰先生对中西文化论战的关切和哲学解答
一
冯友兰先生的“天人损益论”(人生哲学),即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此前在中国国内异常激烈的中西文化论战激起的哲学解答之作。冯先生的“天人损益论”写成于1923年,据《三松堂自序》,这项研究最起码在动机上与回应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1920北大)有十分明晰的因果承继关系。梁先生将中、西、印文化及哲学首先分立开来,分别为它们刻画精神品貌,之后谈各自文化及哲学的命运。这在中国国内学界引起的持久争论,其席卷面之广、实属罕见。而事实上,梁漱溟的演讲,只不过是在《新青年》(陈独秀为核心)和《东方杂志》(杜亚泉为核心)论战的波澜上再加一波,并随着问题讨论的理性化和深刻化,将文化的问题引向哲学问题。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无从吝惜激情、命运攸关地认真讨论的根本性学术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关注,不可能不和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序曲,和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冯先生的首要反思是:中国为何无科学?在题目为《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的文章中,冯先生的“向内”“向外”论,与流行的解释并无区别:早在1916 年,杜亚泉就撰写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说西方人向外,属动,而中国人向内,属静。1921年,冯先生访问泰戈尔,泰戈尔亦有言:“有静无动则成为情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西方能济东方的是活动。”但是之后的学术发展,冯先生便改弦更张了:与对文化差异的关注不同,他开始关注共性,更愿意以历史坐标而不是文化种群的坐标整合和解释差异。他著名的论断“中西问题实际上是古今问题”正体现了这种意愿。
二
《天人损益论》力图根本消解所谓文化差异的终极基础。他选择了“天”“人”“损”“益”这四维的度标,作为衡量哲学产品品质差异的基本尺度、分别代表偏好于“天然”、“人定”、“损道”、“益道”。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冯先生选择了分布于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学派别加以哲学史的考察。并以此证明,中西两种哲学均不缺乏“天”“人”“损”“益”这四种品质要素中的任何一种。至于为什么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个哲学派别偏好“天”“人”“损”“益”中的相关两种,冯先生将之归结于“哲学家的‘气质’和他在某一方面的‘真知灼见’”:
“哲学家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他们的‘见’和‘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有‘见’也往往为其‘见’所‘蔽’……哲学的派别,无分于东西”。
有这样的哲学基础讨论,再回到哲学史与科学发生的关系时,解答自然是合逻辑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是为之而不能;或是能之而不为?……(冯先生的答案)是能之而不为”。从科学和哲学这两项相继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冯先生先是将“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命题的答案预置到中国哲学史中,之后的哲学讨论又摧毁了中西哲学差异的根本基础。这样,对现实的科学发生形态上的差异,如果意欲求取哲学深处的理论解答,就要放弃实在主义的历史解读方式,关注哲学气质和哲学精神。之后被冯先生称之为“照着讲”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治学过程中,我们能显易地看得出实在主义的史实认定和精神气质的抽象提升之间的紧密交织。
三
直到“接着讲”的《新理学》,冯友兰先生方才以其哲学实践的行动,通过对“宋明新理学”的改造,为中西文化及哲学的学术论争给出了属于自己的体系性解答。那么,“新理学”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是坚持“中西”之差别乃“古今”之差别;这样,人类整个的文化系统就呈现一个统一的进化过程,尽管进化的契机和进化的途径是或然的,但总体的进化一致性就可以取代文化差异性,构成解释历史的主流架构;进而,诸如“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类问题,就是文化和哲学系统可回答可不回答、能回答又不能回答的问题:如前所述,它是由哲学或文化流派的精神气质决定的。由此观点观之,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不纠缠于历史、顺着世界文化统一进化的进程,中间道路选择的体系再建过程。
对《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完整评价,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在《新理学》背后所蕴藏着的那种中西合璧的哲学图谋,却与本文的志趣相关。单纯从形式上,我们便不难看出,冯先生的《新理学》是按照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为宋明“新理学”植入本体论基础。这一点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具有西方哲学中心论情怀的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的总体性认识判断有关。正是因为人们近乎普遍接受中国哲学是缺乏本体论基础的道德箴言体系,而真正理解中国哲学的学者譬如冯友兰先生,又分明知道中国哲学的价值内涵富于本质世界的探索,从而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并不远离基于本质世界认识的道理体系,这一中西哲学整体性认知与交流的不对等性,促成了一代具有世界性抱负的中国哲学家尝试用西方人易于理解的观念比附重建中国哲学的体系。不仅冯先生是这样,同时代的胡适、金岳霖、牟宗三,甚至包括熊十力,都各怀思索地挖掘着中国哲学的第一陈述体系,即本体论体系的问题,并且所有的第一陈述方式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学术改宗的倾向,即依托于西方有影响的哲学范式完成自己的哲学史陈述。由此观之,冯友兰先生选择新柏拉图主义作为自己《新理学》本体论根系植入的范式,是一代中国哲人共同选择中的个体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冯先生在时代洪流中的个化特征,很能体现缺什么补什么、裒有余益不足、“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赋中庸哲学以当代内涵的真正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品格。在中西哲学之同作一种“道中庸”的“极高明”,这或许就是冯友兰先生构筑“新理学”的根本动机。
四
从共通人性和共通理性的角度看,大凡人类的哲学活动,都有穿越文化阻隔的汇通性基础,正因为这样,在大的理性尺度上,尤其是在哲学思想作为人类集体智慧递进的发生学尺度上,过分强调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哲学差异是不足取的:所有能够用哲学来名状的恩想,必须有超越现实的本质诉求、一般对象的原理陈述和统一性探寻的属性特征;如果从它所承担的集体智慧萃取、辐射和传承的角度看,哲学的努力又是在追寻一种主动性的思维安全:超越了具体对象的普遍规定性将安全可靠地摆脱具体属性对思维结钩的迷失。由此看出冯友兰先生的“中西问题实际上是古今问题”的宏观论断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带有事实说明功能的有效解释系统,它就必须包含解释显见的差异性之所以发生的那种成分。冯先生曾经带着满怀的疑窦问学于泰戈尔,以及同时发生在国内关于中西差异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就足以说明对中国学人来说,一个有效的事实说明和解释系统是多么必要。本体论是“第一哲学”的核心产物,并逐渐演化成深入于西方哲学乃至科学骨髓之中的精神品格。虽然在西方哲学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轴心不断发生主题变奏,“第一哲学”和第一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化而成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体系,也不断遭到致命性的消解或摧毁,但形而上学的重建和第一哲学的旧话重提仍然是西方哲学基调最准的主旋律。在数学、物理和宇宙学等所谓自律性最强的特别科学哲学领域,只要我们认真地回味像希尔伯特、罗素与怀特海、布劳维尔、爱因斯坦、哥德尔以及宣称寻找一切科学终极基础的康德和胡塞尔,都能强烈感受到一种挥之不去的诉诸第一本质的本体论情结。
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之间的这种割不断的因缘与希腊哲学的终极关怀体系和现实超越之路的选择有本质的连带关系。希腊人十分谨慎于思维的安全,以至于制定逻辑规则从而排斥逻辑规范笼罩不到的领域,如关于善和美的非逻辑判断。谨慎带来了强烈的可靠性诉求,从而怀疑之风日甚,这导致希腊哲学思想的胚胎具有怀疑现象、远离现象的本能。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希腊哲学抛弃现象另寻本质世界的纲领宣言。以脱离现象世界的羁绊为前提,凭借理性沉思实现对本质世界的图谋,在柏拉图那里凸现出一个绝对的逻各斯世界,并与巴门尼德关于抽象存在的追问相合,设定出希腊哲学独有的抽象万有世界,即本体的世界。
如果将柏拉图主义或变种的柏拉图主义作为框架来范畴中国哲学,则有一深刻的悖论:那就是在中国哲学之中,现象与本质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背离,换言之,如果基于本质异在于现象这个基点上,中国的哲学则的确不成其为哲学。中国的先民关注于天人之际,本来将哲学的思考集中于天人融通,当“天垂之象”已经呈现到人的面前而人又对所现之象充满怀疑的话,也就不会出现从卜筮的实践到易理之学到承继发展的先秦子学乃至后来的宋明新理学这样一条顺延发展的哲学轨迹。现象的前身是象、相、文(纹、汶)、兆,这样一组在中国亘古未变过的意义范畴,道和理的观念都从中派生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则象”“卜兆”“观相”都是基于“文”“质”之间统一融通这个基点。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的天文、历算、物候、医学等直接面对具体对象的认识实践中,“文质融通”的基始设定的确是这些理论独具特质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哲学不论面临如何挑战(最突出的例子是佛学的冲击带来新理学的回应)都将在应对挑战中自觉找回的精神品质。
文质融通,或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统一性,导致中国哲学不会像西方哲学那样仅只依靠理性构建空中楼阁式的本质世界。本质世界在中国哲学中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当然也是比现象更优越的思辨对象﹔但由于这个本质世界是通过“垂象”的真实连结与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的,这样,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变成了内外关系:一个被现实锁定的圈内现象世界与包含现实世界的那个至大无外的统一本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或管窥与全豹之间的关系,抑或一个网络同网上的结点、一个场(唐力权的比喻)同场中的局域之间的关系。因此,本质世界在中国哲学那里是一个自在自为但不受终极控制的结构,或自组织自演化的结构,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第一本质的问题,而本质世界也只能用“道”或者“理”这样忠实于结构描述的范畴来表征。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那个至大无外的本质结构的原型就是“天”,“天”的本字为“乾”或“斡”(依闻一多解),就是所见绕“天枢”“斡旋”着的无外周旋体。这样的本质中找不到所谓本体,只有一本然周流的自为结构。为区别本体论起见,这种本质描述的哲学称之为本然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终极关怀,它不会走向本体论,这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体系对于本体论“缺而不能”或“能而不为”、而是中国哲学不需要本体论,因为它有自己的本然论。《新理学》体味到中国哲学本然世界的独立价值,但在对本然世界的论述上却选择为本然论提供本体论基础,我以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思想特征使然。
五
以今天的哲学视野观之,哲学的异质性和汇通性同样都是存在的,并极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不同哲学由于其所持语言体系的异质性,必然导致发生学意义上的差别堆积。在一个特定文化系统的语言结构中所使用的术语,包括概念、范畴和命题结构,往往暗含有待于体悟的成分,而这种体悟,是独立于语言系统的自身规定性而先决地存在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群落特有的共同的兴趣维护着“体悟”的方向,并由这种方向规定着严格语言系统的形戒。成熟语言体系间的异质性问题,正是在这种发生学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求解。正如刘易斯对语言的定义和说明:“一种语言£为一个群体P 所使用,当且仅当在P 中流行着一个£中的关于诚实和信赖的约定,这个约定是由交流的兴趣来维护的。”交流的兴趣所维护的诚实和信赖,正是语言系统的“前严格化”历程中规定语言系统总体走向的决定因素。不论是精密的科学语言还是具有巨大扩展空间的哲学语言,都是从一个不甚需要语言的使用者认真去思考然而又深信不疑的“硬核”―—简约而切要的说理程序和诚信尺度——辐射开来的。这个“硬核”就是我们所说的“质”,所谓异质性,就是指这“硬核”的结构与功能具有不同的内涵,或具有不同衡量尺度的“量纲”,用库恩的说法,它能导致不同范式的语言体系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在中西哲学语言体系的异质性考察中,我们认为西方哲学语境中的“硬核”是本体论,而中国哲学语境中的“硬核”是本然论。因此我们说,所谓的异质性考察,就在于本体论与本然论的关系,包括发生学和结构形态学两种意义。
汇通性是由语言的结构完整性决定的。一种哲学语言有一种语言的长处,包括定义、概念和命题陈述。语言结构规定着人们的思维定式,当有共同的交流兴趣促使人们用同一种语言来传达然与所以然的解释程式时,人们的思维是遵循共同理性标准的。照此意义说,一种哲学体系同另一种哲学体系是难以汇通的,以至于概念的解释、命题的意义、原理比喻的手段,均难以“直接翻译”。但不同体系间的“整体理解”是可以做到的,但理解必须依赖于对体系语言的整体把握。我们能够理解柏拉图、康德、牛顿、哥德尔或爱因斯坦,这不是说我们能够不借助他们使用的专门语言能够将他们的问题说清楚。当我们说“黑格尔的哲学与朱熹的哲学相仿”时,我们是说黑格尔在西方哲学中扮演的角色与朱熹在中国哲学中的角色相仿。整体的体认性是汇通性的前提。基于这种认识,《新理学》的中西汇通还不是宋明新理学与新实在论之间的汇通,而是以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为基本骨架,重新序化了理学的血肉——包括概念、范畴和命题。
六
如果讨论汇通性,我们以为把握各自哲学语言的共同要素是意义重大的。用冯先生《新理学》的陈述,本然的真际与实然的实际,都是哲学讨论的必要课题,不论是中西哪种哲学,哲学语言的“创制”都服务于三个基本课题:1.本然的真际;2、实然的实际;3.本然与实然或真际与实际之间。在这三者当中,本然的真际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在西方表现为本体论或理念论、逻辑学。本然的真际讨论,最本质的特征是用“对任意的什么什么,均有什么什么”的一般形式化语句引导出来的。这种陈述是无特指对象的,或泛对象、一般普适对象的。本体论关注万有的绝对存在,理念论和逻辑关注绝对形式的结构。并且本体论作为元物理学,而逻辑作为元数学。事实上这一点就足以勾勒出西方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可为“科学为什么在西方发生(而不在中国发生)”这个冯先生早期关注的问题(亦即今天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给出哲学上的答案。但这一点。包括冯先生在内的许多人并未过分在意。或许冯先生意识到这个问题,方才为理学寻找本体论的和逻辑理性的基础。但从哲学史比较的角度看,理学中甚至中国整个传统哲学中实在难有这两项基础,因为它们有别的基础,同样充当着一般形式化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形而上的“易理”。“易理”亦可仿西方称之为“元易学”,而具体易学卦画结构的一般形式化原理,有证据表明自从原始甲骨文体系形成之初,便是先民知识传承和交流的核心内容。“教”与“学”的初文均为“六爻”(李圃),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哲学化的“易理”,亦可称为“元医学”,从“易理”——“易学”——“医学”这个从最高的本然原理到一般对象化形式原理到实然经验体系之间的关系构成,正从哲学结构上与西方体系下述链条汇通比照:“形而上学本体论、理念论”——“数学”——“物理学”。从这个关系中我们看出,中国的数学不发达是因为易学发达;机械论物理学不发达是因为有机结构论的医学发达;他们统一到一处,中国本体论哲学不发达那是因为中国没有“第一哲学”,即没有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和一切事物的万源之源,或不将宇宙视之为受主宰的“控制系统”,而是本然的自行化有机系统,概言之,本然论的哲学硬核规定了中国哲学的一般方向。
——摘自《两行逻辑论初稿》,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