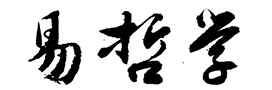在《本然论的哲学旨趣与<周易>解读》以及其他讨论中,我们明确了基于乾坤并建之主题而将卦分族的哲学原则(本然原则),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则是在大族之下的内部谱类之划分原则。
一、两行逻辑论与两行系统论辨析
按照我们两行营卫论的原则,《周易》六十四卦被分为四个族,每一族内部蕴含着不同的哲学主题,而族的内部我们又将其分为五个谱类,随着谱类和谱类之间的不断跨越,族的并建主题不断深化。经过我们之前的讨论,如何将卦按照族的基因属性分为乾坤泰否四族,以及各自的并建主题是什么已经大体明晰,那么每个族的内部谱类又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分别的呢?
对于卦的一个族,二五爻为族定性,决定族谱的基因。从形式上,我们根据一个卦的四个营卫爻的变化数目将一个族分为五个谱类,谱序则根据营卫爻变化数目排序。具体来说第一谱类营卫爻变化为零,即乾坤泰否四卦本身,同时也是四族的开端。然后将营卫爻变化数为1的划为第二谱类、变化数为2的划为第三谱类、变化数为3的划为第四谱类,最后营卫全部异变的是第五谱类,也是族谱并建的尽头。
以上表述是就形式上的分类而谈的,但是需要注意,族谱之分别也并不是营卫之间单纯的数量关系,族谱的分类方式不是一行的集合,而是在大族定性后,紧紧围绕本族并建主题,随着主题的推进而深化的。换言之,主题为基于营卫错配的级别而划分的五个集合(谱类)提供特征值意义的维度,谱类之别形式上表现为营卫爻的变化数目,本质上则是伴随着主题的意义指向而不断超越的。如果借用现象学的语言不严格地表达,则五个集合(谱类)卦体的相似性属事实一侧,族性的并建主题属意义一侧,是五个谱类伴随主题的意义赋予而呈梯度地排列开来展现在我们面前。
为何是不严格的表达?因为西方哲学的现象学是逻辑论的,而中国哲学的道术是两行系统论的。因此在开始讨论前,先要就系统论与逻辑论进行辨析。
从胡塞尔现象学和中国哲学的分别来看,二者的哲学模型尽管都有超越性,但区别也是本质上的。现象学和中国哲学不是同一个哲学模型,现象学是认识论问题、是逻辑论的问题,而中国哲学是系统论的、并建而成理的道术问题。简言之,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本质区别是两行逻辑论和两行系统论的区别。
现象学和中国哲学就主客并建这个视角来说,具有一致性,但并建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现象学要实现的并建之物是自然科学,而且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而中国哲学编织出来的是一个新生态的生命的本然样态,是面向成物之理的创造方式的哲学,是一种发明学的道术。比如人们根据需要,发明了船只,船只是自然世界所没有的,发明是人将头脑中模拟的船只实现出来的过程。而既然自然世界没有船只,那么它就是一个有待诞生的新生事物,这个新事物要实现什么功能?需要满足何种条件?现有的技术要如何将其实现?这是中国哲学需要寻找的。这个事件如果对应我们的主题来说,自然世界有湍急的河流,河流有河流的道理,这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必然;另一方面,人按照自己的需求要设计能够克服急流的载具,这就表现出逆自然,需要人们思考出一套应对之法,而克服急流的道理则是本然之理。
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是如何的呢?不同于科学主义,胡塞尔的认识论也是主客并建的,他在认识活动中将主体确立出来,确立出主体后它与客体是合作的关系,不同于科学主义主观符合客观的“顺自然”关系,科学的本质是主客并建出来的,这是胡塞尔所认识到的。因此现象学不是面向自然本身的本质之思辨,而那个外在的、人们所面向的未知的生活世界,则以符号的形式流注于认识主体。外部世界只具有存在性,符号流进入ego后被赋予意义,并完成现象学的编织,而编织出来的现象学世界才是科学的世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主客并建的认识论于ego的意义赋予来说,类似于“乾”,外部世界流注于ego的符号类似于“坤”,主客之间以这样的乾坤关系达成。但是,胡塞尔这里ego所给出的是让外部世界去符合的意义价值,而符合要以客观性为原则,客观性是科学知识严格性的保证,因此他要让外部符号符合自我规范的同时,也在调试自我去符合外部世界,以达成一种内在世界的纯粹客观性。这就是主客并建的现象学认识论,因此虽然要让外部世界符合ego的观念,但ego的观念是可改变的,ego也在调试着自我以更好的适应外部世界,让外部世界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于ego的观念,这才是现象学的并建要达成的客观性。
那么中国哲学如何对待主客达成的客观性呢?比如,中国人要创造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共和国,毛泽东在延安时候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并没有到来,那么需要如何擘画?这里的客观性的原则要如何建立?纯粹实践的原则建立不起来,有待于检验的由经验论而生成的实践论也检验不出来,那要根据什么检验?中国人的回答是以道术自身的规定性来自我检验,这才是道术的实质。它的核心的问题在于,超出了经验论范畴的那种非当下世界和当下能够澄明的经验世界如何贯通的问题。这也是认识论问题,中国哲学的认识论问题由道术来解决。而西方的认识的问题已经走向逻辑了,到了胡塞尔已经不可回避了,可以说中西哲学的认识论分歧是早在古希腊时就已经形成了,是后来到了康德时期问题被彻底暴露出来,胡塞尔才不得不走向超越之路以尝试扭转。我们认为,认识论的核心就是一个经验世界与未验世界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在时间意义上、空间意义上以及程序上三者共同构成系统论的要素。
系统为什么能够具有当下到非当下的穿透性?不同于逻辑,系统的结构带有普遍性,对于任何一个事物,当将其理解为系统之时都不会犯逻辑学错误,这是中国的道术哲学能够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一问题不被理解之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的哲学有没有逻辑、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不是逻辑的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的逻辑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次生问题或派生问题,因此当人们以次生问题的手段去描述中国哲学“根目录”上的问题,并考察其是否属于逻辑问题之时就一定出问题。而实际上,在未生成逻辑之时,中国哲学先生成的是系统,系统论优先于逻辑论,这是中西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中国哲学首先生成系统观念,而西方哲学则首先生成理念观念,在逻辑上就是共性与殊性,也就是 yes/no 式的观念,要么符合要么不符合,而在这样的观念下,系统是无法理解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不以系统论角度看,河流是变化的事物,只要其在时序上发生变化就成了不同的事物。因此就西方传统文化来说,不可能认同系统就是流变的永恒统一之物,因为它不可被 to be 表达,因此不可设想。对于静止的事物也同样如此,哪怕两棵同种类的树,其中一棵比另一棵多了一片叶子,那么在这种哲学中就一定不是一个事物。简言之,无论流变或静止,只要比较的两者不全等就不行,所以他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必然的原则。这就是个系统论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科学爆炸之时系统论会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这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一种重大突破。
二、基于两行系统论为族划类
经过上述讨论,系统论是中国哲学道术的特征,而这才是我们对谱系分类的本质依据。在具体描述谱类之前,我们先以一个具体例子来引入。
我们比较《易》作者对家人卦与渐卦两者的描述。家人卦(䷤)在我们的谱系结构中,位于否族第四谱类第一位,营卫爻除上爻外其余三者都发生了异化,该卦距离行否的两行组织结构之崩溃已经近在咫尺了。家人卦,从卦爻辞来看,无论是卦辞的“利女贞”,还是爻辞“富家”、“王假有家”等,《易》作者都暗指是在国家以上层面难以解否行泰,但在低级的家庭层面可以作到融融之和,从大国的命运擘画到小家的利益谋求,共命运体的架构逐渐瓦解为人人为私的境况,可见在《易》作者看来家人卦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但我们再回到并建的前期,渐卦(䷴)位于否族第三谱类第一卦,如果我们脱离谱类问题而直接比较,似乎家人卦的否行共命运体结构比渐卦更加稳固,因为仅从两行的实力对比来看,家人卦的阳爻共同体比渐卦还多了一个初爻,似乎上行架构更稳固,那么按照社会结构来说,似乎理应是家人卦比渐卦的共命运体更强力,社会架构更稳固才对。但是显然,渐卦以“鸿渐”为引导,表达的是否行社会下不同社会成员不得不承受的境况,也就是说正因为上行的刚愎自用仍旧强而有力,两行命运体以刚愎的形式得以安稳,这才使得其他成员的默默忍受成为了不得不然。家人卦的阳爻共同体成员更多,但反而体系不够稳固,渐卦反之,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经过我们前面的讨论,出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卦的讨论不能脱离所在谱类,这是中国哲学的两行系统论所决定的。回到这个例子,对于否族来说,对上行结构行否最有利的营卫结构是否卦结构,而相比否卦一旦营卫结构改变,这本身就是对该族行否的完备条件的破坏。这个破坏是营卫结构的改变本身决定的,这个更本质,而不是改变营卫对上下两行的天枰在哪里加砝码的问题,即营卫对上下平衡的影响是表,而结构变化导致远离否族起点这件事才是里。
我们按照营卫结构的改变而设谱类,原因就在于每一个营卫变化对该族最初的政治条件都朝着不利的方向去发展。因此无论营卫变化表面上让两行关系的重心偏向哪一侧,偏离初始卦这件事实本身是不可逆的,而营卫条件改变越多,系统距离初始条件就越远,而这件事正是遵循着族本身的并建主题向前衍进的,它的不可逆性与一族主题的不断深化互为表里。
因此谱类本质上就代表着一个两行营卫系统随着并建的深入,对初始条件的偏离程度。我们对谱序的定位还是取决于两行的互动,而不是把具体的哪一个因素作为因果关系中的一个重点,系统论中我们避免建立一个第一因的概念。在系统论中,如果用因果逻辑的追问方式去寻求解释就会陷入到一种机械的解释论。虽然营卫配比的变化影响了阴阳双方的力量对比,放在谱序中看似乎也可表现出来,但是在我们表达之时真正要强调的还是营卫重组的程度远离初始条件的本质。因此对于两行营卫论的说理体系,我们的解释理路是通过营位结构的改变来说明因果关系,是营卫的“结构”,不是营卫的“比重”,在《易》的四个不同的族中,营卫结构的改变都不同程度地决定着衍化的层次,营卫的比重不本质,结构才本质,这是系统论所决定的。
进一步来说,营卫就是结构,它与两行结构是等价的,在两行营卫论中,两行是一个结构组,营卫也是一个结构组。每个谱类都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集合,为了将这些谱类关系清晰表达,我们在谱系排列的时候并没有将这五个单元表达在同一层级上,而是将不同谱类放置在不同层级上,这样,一个族谱从左至右将并建主题的深化过程直观化,而从上到下将五个谱类呈梯度排列则是将系统的结构变化的衍进过程直观化。这样一来谱类的分别就如同四季,尽管秋季的气温有时甚至超过了夏季,但不能说那一天就是夏天,因此营卫结构变化更本质,营卫比重变化更直观,二者的关系就是如此,即在系统论中结构的优先级要更高。
总的来说,在我们的谱系划分中,一个族的五个谱类就是五个集合,但集合在更为本质的族的系统关系下,按照意义而分梯度排列。因此对《周易》六十四卦分族分类,按照爻的变化排列组合这是表,而主题决定的内在关系是里。所以在系统论系统优先的前提下,解读一个卦必须识辞归族,并且具体来说要放在族的具体谱类之下,因为本然论不可脱离关系,而关系不可脱离系统,这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将六十四卦按照这样的谱序排列,那么在解读之时我们就拥有一个可靠的尺度,一个基于道术的标尺,就不会产生歧义和混乱。而将卦纳入族谱之中,卦的本然态势就已经直观地呈现给我们,而反过来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式检验《易》作者内心中想要表达的道术观。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说理方式,能够能向着《易》作者心中所想表达的更加靠近,我们以这种方式将卦排序,就是要通过谱序结构来证明这一点。就像前面的例子,渐卦和家人卦如果不是放在谱类之中,营卫配比的表象和《易》作者行文中表达的内涵就无法对应。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说理体系,那么一个《易经》的六十四卦就是杂乱无章的,而各家对其解释也多种多样,看起来哪种解释都有合理之处但又多有牵强,让人不知如何把握,解读不得要领。我们希望通过回到中国哲学的道术问题、回到中国哲学的基因中去寻找方法,用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将《周易》的内涵厘清,并在当今时代实现现代化的合理表达,这是我们的学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