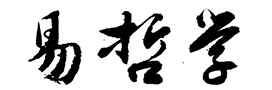在一个卦中,我们以二爻和五爻为卦定性,通过二爻五爻的不同我们将《周易》的六十四卦分为的四个族谱,即乾族、坤族、泰族、否族四大类。在每个族的内部,我们再根据营卫爻变化的数量将一族之卦分为五个谱类,每个谱类中再根据营卫爻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排序。这样一来就将八八六十四卦以两行营卫论表达的方式凸显其内在逻辑,以便《周易》的内涵得到清晰化表达。
因此,我们对卦的讨论以及易哲学很多的问题都要还原回这个谱系上,才能够以两行营卫论的方式给出清晰回答。以乾坤两族为例,其主题凸显的是“乾坤并建”。所谓乾坤并建所表达的内涵即是开物成务,“开物”一侧由乾所决定、“成务”一侧由坤所决定;“乾”的一方提供的是基因意义上的生命程序,“坤”一方提供的是该生命程序所依赖的数据载体。只有“程序”与“数据”合作才能完成乾坤并建,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点。围绕中国哲学的这一本质特征,我们还需要一些澄清,明确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以辨别中西,并坚持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基点而展开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而不应简单地以“中学西范”的方式以西学之“医”调理中学之“体”。
在我们所谈论的哲学当中,中西哲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中国哲学是本然论的,而西方哲学是本体论的。造成两种文明分别以本然论与本体论相区别,其关键在于作为不同文化之前提的终极关怀,这也是哲学的第一本性。显然,西方哲学的终极指向彼岸的世界,而中国哲学指向现实的关系。
本体论所究问的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本质,因此我们可以用本体论来概括西方传统哲学。第一,它究问的是存在、存在之所以存在即存在的所以然。因此它以存在性为理论的切入点,追问之所以存在的本质,这就诞生了存在性的形而上学。第二,它要找到一种绝对的本质。为了确立这个绝对的本质,这就必然要把行而上的世界和柏拉图意义上的彼岸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的上帝贯通。这样,存在性就是他们所究问的原初;存在性的终极本质,即实体,则是关于上帝性的一种分有。这就构成了在康德哲学之前所形成的西方哲学不二的一个理论范式。因而,如果对西方哲学做一个高度的概括,那就是本体论的,而对本体论进行概括,则在于两点:第一,它是基于存在论的;第二,它是基于终极的上帝的或是彼岸的。
明确了这一点,则可辨析本然论之于本体论的根本区别。首先最大的不同,本然论所究问的东西绝不是存在性,中国哲学所究问者若也借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描绘,则是“存在间性”,即追问的是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系统。本然之“然”,它是一个对诸多存在之发展样态的一种表达。比如生命体,它在中国哲学中被理解为一个诸多存在物之间形成的高级关系体和高级存在物。比如人的身体有五脏六腑诸多脏器,它们当然是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性表现为在两行视域下的作为关系体之中的存在性。因此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生命体,它究问的则是一种综合关系:即生成了什么样的关系、生成了什么样的功能、生成了什么样的价值和生成了什么样的意义。
存在性的究问是顺着作为对象的某个物向着深处、向内追问,而关系性的究问则必然需要关系的两个节点。因此我们说,本然论的出发点是存在间性而不是存在性,由存在间性生成关系、生成功能、生成价值、生成意义。关于这一点,在中医的范畴下很好理解,经络意味着一种功能,作为生命体所需要的功能,只有经络通畅我们的生命才具有和谐运行的保障。中医所描绘的经络是连结内外的,其向内着落于脏、腑,向外则延申至我们手脚的二十个指头。因此经络是一条线,连接着内外的结点,经络的哲学本质就是脏器与生命体外部之间的内外间性,这就是关于经络的追问。只有从间性向外追问,我们才可获得关系存在的本质,由这个关系存在的本质,我们才能够究问一个系统或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之缘由。
这样,本体论与本然论的究问方式之不同就很清晰了,两者可简单概括为:本体论的究问方式是“存在之所以存在”,本然论的究问方式是“然之所以然”。如此的功能组合就达到了如此的系统样态,这才是本然论对“形而上”的表达方式。因此这种关于诸多的间性的追问形成了本然论的理论核心,这样,现实的系统、生命、事物等,都在如此的追问下获得解释的依据。正因如此,中国哲学将“所以然”作为形而上,以“然”作为形而下,这样形成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才避免了上帝与彼岸世界的悬设,才没有走向本体论的世界。因此,对中国哲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道器关系亦可表达为:“所以然者为之道,所然者为之器”。
在本然系统当中,既然中国人究问的是间性,那就要区分与之相对的对点性的究问方式。间性在逻辑上可设置为三个点,若区分其为A、B、C,则两端是A、C,而B在于AC之间。存在是点性的存在,其究问是点性的究问,则存在性的追问最终指向ABC三个点,而本然论究问的是间性,那么就绝非三个孤悬的点,因此间性的究问必然指向两行性。这就是本然论和本体论的原哲学基础,本然论究问“然”、本体论究问“体”,本然论究问的是一种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其构成的本然体系。
在本然论世界中,对于功能性和间性的追问方式生成了两行论。这样,如果对一个功能或一个物的生成进行追问时,本然论给出的答案则是开物成务。这意味着开物者和成务者不可或缺,开物者如同一个程序的空形式,而成务者如同纯粹的质料,该质料自身不能动而程序能动,只有二者结合一起才能够生成事物。所以本然论所谈的功能之间的关系,与现实世界中事物的如此这般的表现之间构成了一个自洽的解释系统。
以上的论述是我们对易哲学解释的理论出发点,而对于《周易》所表达出的乾坤并健,在我们确定“乾”与“坤”两方的开物性和成务性之后,则可以看到乾坤并建的本质正是两行并建,两行并建是一般表达,乾坤并建是两行并建在易哲学中的具体体现。乾坤的并建在《周易》中生成卦,一个卦的生命状态的好坏则需要按照本然原则进行追问,即回到卦本身考察卦的营卫状况、考察诸多的功能呈显为怎样的状态,这就是考察一个卦的本然之态。两行营卫论的讨论是在本然论的框架下的,而本然论的框架是给现实的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提供理论依据,即给出一个因果推论的原则。有什么样的本然关系,那么它的现实的系统大体上就应该呈现出什么对应的样态,这也决定了其呈现出何种趋势。
该主题在我们的另一篇讨论中还有进一步的延申,可参考《易哲学院主题讨论之——孔子的思想特点》的讨论加深理解我们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