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命运体与共命体的关系问题,在《易》的体系中表现为上下行之间的两行关系问题,这被中国的早期思想家视为最重要的基本问题。这里所述的早期思想家并不是指春秋时期的儒家和道家,而是以《易》作者的成书为代表的那一批思想家,他们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这种思考通过经辞设计的方式表达出来。《易》作者将殷周之际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等革命形态所形成的新思想,以《易》的经辞设计为载体,通过周易的卦画这个“旧瓶”装了进来,这也就标志着中国的文化进入到成熟的哲学化时期。以后的学者一直将《周易》奉为群经之首、六艺之源,正是因为中国哲学的早期思想胚胎就发殇于《易》中,这是一以贯之的。
之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始终围绕着礼乐崩溃之后,人类社会朝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仍然是处理命运体与共命运体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易》哲学的基本问题,两者并不偶然地耦合在了一起,那么两行共轭思想和两行和谐的理想就作为一种思想共识而奠基于《周易》当中。
一、“心无为而制窍”的理论初心
《管子》书所处的时代,是从周的一统到天子被架空而进入春秋的这样一个时段,也就是处在从周的礼乐体系向春秋制度演进的关节点。因此管子是春秋前的思想家,管子尊天子,因此管子在世之时还不能说入了春秋,而管子死后齐国发生了政变,这个时候才实质性地进入春秋。这当然不是从断代意义上说的,而是以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判定的。与管子相比照,孔子就是春秋向战国时期过渡的思想家,是春秋之末。因此春秋早期的思想家以管子为代表,春秋末期的思想家以孔子、老子为代表,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也有所不同。管子时期的礼乐文明将崩而未崩,因此对管子来说,问题在于为何要构筑礼乐文明、上下两行之间为何要有理论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以及为何会有两行和谐的共识性的思想,其以何为基础?因此,我们将管子的反思提炼为:早期思想家的原始思想的合法性的澄清。
管子常常将周公之前的儒家与周公之后的儒家对立起来,前儒家以《易》作者为代表,后儒家以周公为代表。管子以原教旨主义的前儒家思想批判周公之后的儒家思想,认为周公没能将国家的顶层设计问题处理好。自周公起,西周的礼乐文明建构就走上了一条斜路,以至于到了管子的时代,他看到的是礼乐文明的将崩而未崩,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管子所思在于,周公之前的哲学思想是基于何种理论合法性设计的?而“心统百骸”、“心无为而制窍”,以及心术、理万物的思想都出自于管子。对管子思想进行如此的还原,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管子没有谈《周易》,但是管子的思想与周易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思想是相契合的。
“心统百骸”、“心无为而制窍”是管子的重要思想命题,心相当于中央政权、百骸相当于诸侯,因此心术的“无为而制窍”与礼乐文明的哲学设计是一致的。而礼乐文明既要保证农耕文明的富强,又要让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地方、地方与国家政权这样诸层次的两行关系和谐。因此“心无为而制窍”就是管子得到的答案,即以心统百骸的无为而治为标准实现两行和谐,而这种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医家思想是一致的。医家的心和百骸的关系、心和脏器的关系,就如同国家的中央政权与诸侯、诸侯与其下的其他子结构之间的逐层的两行结构之关系。
然而,在一种两行关系之下,如果没有下行基础的稳健和牢靠,上行结构的乾健则是不可设计的。另一方面,管子也特别强调上行结构的职责,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站在上行结构进行恰当性的整体擘画,并对下行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这样才能“仓廪实、知廉耻”。知廉耻是儒家的“高级词”,仓廪实才能知廉耻,上行擘画做到这一点,国家的存在才具有理论正当性。因此管子强调的是,作为为上行擘画的君子就需要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天子就要拿出天子的担当为上行擘画、为下行提供管理和服务,力求构造一个和谐的上下行关系以达到下行的普遍强大、稳定和牢靠,让其如水一样承载上行之舟。这样才能为共命运体的健康前行提供必要保障,而这,正是孔子儒家所缺乏的。
二、荀子“礼待圣人作”的哲学要旨
在管子之后,对于礼乐文明的重构,荀子发出了“礼待圣人作”的感慨。荀子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任由下行结构自由演化,那么终究不能生成健康的共命运体,只有上行的圣人之作与下行的依靠自身规律而健康成长,两者相向而行、上下并建才能实现两行和谐与健康。这种思想显然是《周易》关注的核心,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哲学的根。相反,一旦上下行之间关系失衡又不能做出及时调整,那么社会系统将远离健康、表征出病态。
所谓圣人之作,当代人已经对此十分反感。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荀子所讲的圣人之作并不意味着呼唤着一个万能的人才开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处方、构筑永久的和谐。如果与马克思的哲学相比照,则可看出其一致性。马克思所表达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两行关系,即上下行之间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下就表现为:下行结构决定上行结构,上行结构又反作用于下行结构,这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要领。因此对立统一的思想与两行并建思想在本质上是共通的。“一劳永逸”性暴露出了周人制礼作乐的问题,因此管子的理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要注意的是,管子强调的那个礼乐制度设计之初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能够生成一种好的制度。尽管周人制礼作乐存在一劳永逸地让两行和谐的图谋,这也导致了很多的问题,但我们更要注意到祖先构造礼乐制度用心何在?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它要给人类开出一个太平,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再看荀子讨论“法先王”与“法后王”的问题,强调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当上层建筑本身不能够完成自我革新之时就认为存在着一个最好的政治制度,然后就能够一劳永逸地做到永恒的两行和谐,这就过于“一厢情愿”了。因此荀子所言之圣人,要实时的对上行结构进行跟踪评价、诊断,并适时地给出调整(治疗)。
总的来说,这个“圣人之作”应该包括两个基本的要求:
一、要对两行关系的健康与否进行自我系统诊断,这就意味着针对这一哲学问题要给出命运体与共命运体关系的理论维度,并始终要保持状态追踪和诊断服务。
二、基于这种诊断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调理权变,这也是管子思想和荀子思想的一个主轴,即扶正祛邪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管子给出的“理”的范畴就具有这两个属性。
如此,将周公之前的《易》作者,周公、管子、孔子、乃至于荀子的思想串连起来,从殷周之际到周秦之际,中国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与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具有一致性,而这一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其生成与深化都与《易》相关,是《易》将基本问题引申出来,再经由诸子们发扬光大。因此,明晰《易》哲学问题的两行营卫论属性,中国哲学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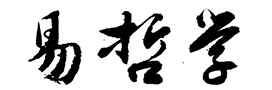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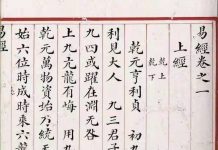
而这个“礼待圣人作”,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圣人基于对“天人之际”的把握,立足于“下行结构”,构筑“上行结构”,在上下行结构的良性互动中,既引导下行的良性发展,又反过来对上行结构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以此确保共命运体和命运体的健康发展?
非常感谢您的阅读,从您的回复中我们看到您已经十分理解我们的主题了。没错,圣人的制礼作乐就是以为两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其理论合法性的,这要求“上行结构”与“下行结构”相适应,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被表达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圣人如医,医者的“治未病”需要对两行系统实时跟踪评价,当两行结构不相适应之时就要对其诊治。因此圣人制礼作乐的关键就在于:要以对共命运体未来命运的乾健展开为目标进行综合性的把握,以两行命运体之展开的最优解为标准进行理论擘画。
再次感谢您的思考,如果对我们的主题感兴趣,十分欢迎您在我们这里继续分享,如果我们的主题对您能有所启发,也欢迎您向我们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