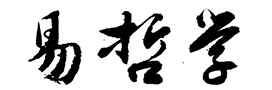一、生态哲学前提下的历史反思
生态哲学是现代工业文明反思思潮当中的哲学领域之一。唯因如此,生态哲学染上很浓的反思哲学和批判哲学的气息,特别是以工业文明为对象的否定性批判的气息。但是,在林林总总的以工业文明为对象的反思哲学当中,生态哲学在基本内容上又蕴含着远比反思和批判更深沉的内涵,这内涵是在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哲学元思:人类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人类与之互动于其中的世界?与其说这是生态哲学内涵毋宁说这是所有哲学必须深沉面对的纯哲学内涵:我们又和我们的祖先贤哲站在了同样的思想地平线上。
但生态哲学又不仅只具备这种元思的内涵,而是又包括了另外一项追切的主题:为工业文明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寻求切实和可行的归宿:这就超出了反思和批判的范畴,而对未来给予体系化的思想建构。这又意味着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难以为真正的生态哲学所容,建构的迫切性拒绝任何形式的“深刻的片面”性。换言之,生态哲学能够容许在思辨尖锐性方面做出牺牲,而不能容许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相结合,在“人——工业文明——自然”之间建立新的对立,给人类的未来开出极端的行为处方。这就如同面对疑难杂症的病体不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治疗一样,生态哲学的当代使命是对“人——工业文明——自然”综合体给出全面的组织诊断和组织修复建议。
本文认为,生态哲学的当下发展,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三项历史使命:其一是为自然的辩护,深刻地指出了本非被动地位的自然界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进程面前事实上处于了被动地位;其二是批判性地反思工业文明,指出在工业文明以前人类中心主义并未酿成重大生态灾难,是工业文明且唯有工业文明,能够如此显著地使自然界的被动状态有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的危险﹔其三是挖掘了违背生态伦理的人类中心主义根源,孕育了工业文明的两大思想基础处于反思的焦点地位:基督教“自然为人所设”的宗教观与“主客对峙”的西方哲学观被认为是与生态文明南辕北辙的理论渊薮。这些认识的深刻性足以标志迄今为止生态哲学的历史成就,以此为基础的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立法也在讨价还价的争吵中浮现出来。但是平心而论,生态哲学为当代人类的贡献,警世的深刻性有余而禁得住充分论理推敲的建设性不足,尤其是极端的生态哲学理论,更是用苍白的理论试图解构积淀几千年的文明、或试图用生态文明的境界开示捆绑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本文认为,生态哲学一旦进入反思与批判、批判与解构、解构与否弃的理论怪圈,便是与生态灾难等量齐观的人类文明灾难。故而否定这个意义上的理论呻吟与生态宗教的怪异践履,而是主张“文明责我开生面”的新人类主人公意识,重新将“文化生存的人类——人类自主的文明——文明耦合的自然”纳人新的物质精神家园的和谐世界的创造性构建体系当中,为人类的后工业文明指明自主自为的方向,帮助和规范工业文明纳入生态文明的共输轨迹。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绝大多数,以民族的生存性着眼,看到了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不能原创地发生、也不适应于已经发生了的工业革命的“文化性”的一面,为了民族图存,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削足适履的自身文化反省运动,纳人了以廉价的“世界工厂”身份参与于其中的全球化工业文明进程。而这恰逢中国参与于其中的三十年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正是生态文明的认识从懵懂到觉醒的三十年,也正是生态哲学阻遏工业文明继续发展的思潮泛滥发展的三十年。与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关系不大但大受忽略的是,中国人对工业文明“削足适履”的“原足”,恰恰是在原发的早熟的觉醒下的生态哲学。我们非有意为这段历史公案断是非,但我们既定性“极高明道中庸”的中国哲学为早发的生态哲学,就应该进人中国哲学的内部,既历史性地发现其生态哲学——其实是广义的生命哲学——的思想史资源的价值,尤其是以“赞天地之化育”“叹文明之璀璨”“尽人生之天年”为哲学风骨的基本品格,也应该现代性地发现其工业文明诊断的价值。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体两面,历史永远是现实的镜子,唯因中国哲学是历史上最纯粹的生态哲学,我们才有必要认真地审视它,按照生态文明未来建构的当代要求,发掘其可以转移再生的思想原理,为中西合流的生态哲学提供无需思想试验的宝贵思想资源。
二、生态哲学的历史
生态哲学的历史是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启的。如果像生态哲学家们所作的思想史探源,则思想的先驱在于二十世纪初的科学与社会危机的反思运动。对像阿伦·奈斯这样的哲学家来说,则更愿意将自己的观点与斯宾诺莎、海德格尔;甘地、佛陀与老子等“生态哲学”的先驱用哲学的逻辑串接在一起,也只能是属于“六经注我”的大智慧范畴,而与生态哲学历史的书写无关。
我们反思生态哲学的历史,应该有一个思想成熟的框架尺度,并用这一思想成熟的框架尺度来界定历史上的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发现的性质、作用、地位及意义。这需要对生态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进行超越历史的省察。生态哲学应该包含三个理论递进的基础部分:知识对象的生态系统研究的哲学纲领;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互动过程的交互组织机理及其综巨系统衍化过程中的结构逻辑﹔人类与生态的共扼命运反思及生态伦理的确立与实施。
如果用这样的生态哲学观念审视真实的当代生态哲学的历史,不无遗憾的事实是,当代工业文明是在错误的生态认知理论纲领的指导下,在无视“人—生态”交互组织机理和过程化结构逻辑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固执下引发了生态灾难之后,方才病急乱投医地展开生态哲学特别是生态伦理的沉思。也就是说,生态哲学的发展历史,生态哲学的理论发展史,是按照理论递进的逆生逻辑而展开的、缺乏理性沉思但急于感性革命的速成思想体系。它的理论内核十分简单:大难当头的人类应该无条件接受约束人类自身的神谕十诫。由此,生态哲学并未朝着将“文化生存的人类——人类自主的文明——文明耦合的自然”纳入新的物质精神家园的和谐世界的创造性构建体系的理论纵深发展,而是把神谕十诫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宣扬成为新的人文精神,简言之,生态哲学正作为基督教的替代物和补充物即生态宗教而体系化自身,其理论的优点和体系的幼稚都从其宗教化的特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当然,这是针对当下生态哲学的主流而言,并不是说没有纵深化理论发展的趋向。实际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成员们正在着力扭转这一宗教化趋向,使生态哲学更哲学化或更科学哲学化,也就是说在生态哲学逻辑基础地位的前两项内容上试图取得真正的理论突破,但整体的理论进展还远没由成熟到现实的迫切要求,故而尚不能为当下的生态哲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历史地看,生态哲学的理论进展遵循这样一条逻辑发展轨迹:
(一)发现性地反思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极限——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在今天看来,这更像是当代版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因为它们所共同揭示的增长过程趋向化的“所取”与“所与”总量上的矛盾,所不同的是,人口理论基于自然生态模式而增长的极限理论基于被工业文明的技术杠杆加速化了的增长进程。虽然两种理论的核心本质上同一,但同一深刻主题在不同历史前提下的变奏总能表达出感人的乐章。但两者的更加共同之处或共同的理论弱点都在于:将对人类文明衍化的自发性加以责任化灾难规避的解决方案诉诸人类的伦理自觉。事实上正是这样,当代生态哲学中一股重要的极端分支,就是将“天赋人权”的理论主题不加反思地运用于动物、植物乃至自然界,形成“宠物权”“动物权”“生命权”及其“自然界自为权”等生态伦理道德立法活动,并冠以“深层生态观”的新人文境界,演化出林林总总的生态伦理教义的行动组织和新宗教派别。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为响应人口理论而将生殖与婚姻、家庭、性相剥离的不育运动,实质是将一个极端转嫁到另一个极端。这并不是人口理论和增长极限理论本身的错,更不是这两种理论的深刻性的错,而是理论本身的不周全和问题解决方案带有消极化倾向的错。
(二)反思到生物圈的自为存在被人类的征服能力所“忤逆”破坏。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是杰出的代表。这是一个站在人格化的生态系统——生物圈或大地母亲——的视角上对人类文明史综合梳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演绎史。其生态哲学的深邃立意不能不让人高山仰止:“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围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汤因比,1992,第10页.)然而纵观人类文明,汤因比的结论是:“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第一个这样的孩子。……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力量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了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的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间上,第20—22页)基于此,他的结论是: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恐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上,第10一11 页〉
如果说生态伦理具有逻辑意义上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在善恶两分的逻辑前提下汤因比的论述具有终极的意味,这是欧化版的“性善论”脱离开上帝与本体论假设的最完美证明和表述之一。它是以生物圈这个大地母亲的固有属性为起点导引开来的。因此,就道德化的生态伦理理论基础的奠基而言,汤氏的表述是无所出其右的最经典表述。
(三)反思到工业文明的技术属性和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相结合所孕育的必然矛盾将在全球化过程到来之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总体爆发。欧文·拉兹洛原本就是罗马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布达佩斯俱乐部的“第三个1000年:挑战与前景”是拉兹洛的新的科学、社会及文化反思之作。闵家胤这样介绍和评价了拉兹洛合同的布达佩斯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起陆续提出的十几份报告)其基本含义是:随着世界各国仿效欧美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各国经济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出现了三个负效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可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惊醒世人之后,并没有提出解决全球问题和避免灾难的办法。罗马俱乐部成员、系统哲学家拉兹洛在完成罗马俱乐部第六份报告《人类的目标》之后突然醒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的外在极限均是一些常数,难以改变,现在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逼近这些常数并可能引起灾变,过错不在地球,而在人类自己,具体说,在引导人类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和价值,而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他转向对西方文化和价值做批判性反思,并写成了一本书《人类的内在极限》。”(《广义进化研究丛书》序言,2001)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解读出拉兹洛从罗马俱乐部思想群体当中“突然醒悟”出来的思想基础是“问题的解决”,而问题解决的哲学出路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的批判。严格说来,排除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名气所具有的传播效应,这种思想觉醒丝毫不具备哲学的原创性,远远在于汤因比的思想之后和之下。甚至也可以反衬出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家严重忽略了技术社会之外的思想反思运动,例如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反思运动。但布达佩斯俱乐部(成立于1996年)思想家群体帮助拉兹洛完成了又一次的思想转向:从文化批判走向全面的文化修正。
在本人的理解之下,拉兹洛为布达佩斯俱乐部撰写的第一份报告有如下的思想突破:其一是,西方哲学对历史是有悖于生态哲学的历史。他写道:“逻各斯加测量,希腊人向西方文明提供一个以后2500年一直向上建构的基础。这不是没有质量因素的一种数量基础。在希腊人推进的认知图像中,人类,及其某种程度上一切生物,有不包括在数量性质之内的特别的价值和美德。逻各斯和测量与美德的组合产生了一种情感和一种伦理,其中人是尺度而发挥人的潜力则是目标。”(拉兹洛,2001,第114——115页)这是一个极有发生学韵味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哲学起点论述。接下来所论的基督教和科学技术的兴起,在同生态哲学相关联的核心观念上,找到了真正的非生态哲学的逻辑起点。
其二是,人的美德发挥形式与技术能力的展现形式偏离了生态化生存的人类轨道。报告中写道“琼斯们,莱昂哈德们和伊藤们(世界的贵族代表,引者注)生活和消费的方式并不符合大众的利益,甚至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仅使用了世界能源和原料的80%,而造成最大份额的污染,它们也破坏了他们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恩高们(世界穷人的代表,引者注)可能必须走两英里才能得到安全的水,如果他们确实得到任何安全的水了的话,撤哈拉以南人民的48%得不到饮用和卫生用安全水。”(同上,第21页)这样,在“富裕的负担”和“贫穷的苦难”的对比标题下,拉兹洛试图申明,工业文明全球化扩张导致的当今状态,与其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极限的紧张,毋宁说是贪婪化生存方式造威的人类自身的关系的极限化紧张。这不是人类或人类行为的量的增长的问题,而是人类质的贪婪造就了竭泽而渔的行为方式或品质习惯。只有改变关于人类美德的定义和展示方式,人类才能回到生态哲学的正确轨道。与人类被告知在灾难的边缘化生存的警告不同,新的生态哲学认识表明人类有自己修正自己行为方式而回到生态文明轨道上的自由度,这种积极认识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来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三也是报告的最深刻之处是,地球生命必须被科学作为整体生命来描述和对待。这种科学哲学观的改变实属不易,但布达佩斯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决定在科学的核心地带重建生命化描述的新物理学。众所周知,迄今的物理学奖包括地球在内的宇宙物质世界描述为不带远程纠缠效应的物质与能量的孤立存在。这正是机械论宇宙观的逻辑基础。而在机械论的宇宙观下,物质世界与生命世界是截然分离的,唯因将包括地球在内的物质世界当成“死的存在”,生态系统才被误认为是“资源”的化身,可以随意取用和挖掘。如要改变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必须将分离体之间的超空间纠缠——物质交换、能量交换与信息交换,表征为物理学可行的原理基础。为此,布达佩斯科学家们重新解释了真空:它不应该被理解为“空无”,而是应该重新界定成以太——一片含所谓物质世界于其中的超级能量之海(同上,第151一168页)。
其四是,其他一些涵盖于上述基本认识但有所发挥的一些深刻认识。例如,反思到人的自我救赎方式不能在基督教文明的思想框架下“生态人”自我实现——奈斯的“深层生态观”﹔反思到生态伦理的失范是人类一切道德伦理失范的最高级、也是最集中的表现形式——生态女性主义(奥波尼的《女性主义的毁灭》);反思到生态学—布克钦“非中心化的、无国家的、艺术的、集体主义的、完全自由的社会”;反思到生态毁灭与人类毁灭的共命运关系——汤因比,奈斯等﹔反思到拯救生态危机的必要性——拉兹洛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报告及行动纲领。……
这个过程还可以列出更长的清单。但迄今为止的思想足迹在两相之中跳跃性徘徊的特征也已明显:其中的一项是“警世恒言”,即把生态危机和危机的后果渲染得淋漓尽致;另外一项就是“人性救赎”,即用“生态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抑恶扬善古训烘托出“生态宗教”。“让自然寻求自身的平衡”的“生态中心主义”正向生存与发展之间艰难选择的当代人类发出“生态公民”的“道德十诫”。
如果将生态哲学的镜头过分关注如上的思想舞台,那将意味着生态哲学很难告别他的童年。因为他的反思更多的浪子回头的励志:这是在危机来临面前的“他觉”醒悟﹔而一些激进的生态哲学先锋,譬如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学及绿色和平组织,则是人类在“出埃及记”的逃难途中的英雄摩西。如果当代的摩西们拿出的不是理性自觉的生态哲学纲领,而仅只是“十诫金牌”,那么人类对他们的敬意将远远逊色于圣经里的真实摩西。哲学一向视宗教为自己的童年,告别童年走向成熟,生态哲学方能够从“他觉”走向“自觉”,从幼稚走向成熟。
三、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对当代生态哲学的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之后,我们应该摆脱掉生态哲学当中的“他觉”和批判意识,严肃而正面地提出生态哲学的真问题。这之前我们要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宗教”的伪问题,那就是人类的第一要务是归还生态的“自为权”和捍卫“物种的多样性”。它的“伪”不在于其缺乏正当性,而恰恰在于一种极端情形能够反衬出的悖论:人类如果毁灭,那么地球生态不会毁灭,相反、地球生态真正的“自为权”从未放弃行使,没有强大人类的物种多样性永远可以自觉恢复,直至地球生命的自我完结,正像一个自然人的死亡绝不会导致人类的灭种一样。换言之,除非人类“忤逆”到充当暴徒炸毁这颗星球——人类确有此能力,地球的生命将由地球自身而非人类所规定。明白这一点,我们便会成熟地明确生态哲学的一个前提:寄居于地球的人类的生态相关活动的开展,仅仅面向人类自身:生态哲学的本质是经营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如果将人类这个生态同命运体理解成一个生命体,譬如人,那么生态哲学的沉重主题实际上约化为:如何与环境“共轭养生”。
前文已经说过,将“文化生存的人类——人类自主的文明——文明耦合的自然”纳入新的物质精神家园的和谐世界的创造性构建体系当中,为人类的后工业文明指明自主自为的方向,帮助和规范工业文明纳入生态文明的共轭轨迹。是生态哲学的综合目标和基本使命。以此为圭臬,我们也曾将生态哲学归结为如下三大基本问题:知识对象的生态系统研究的哲学纲领;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互动过程的交互组织机理及其综合系统衍化过程中的结构逻辑;人类与生态的共轭命运反思及生态伦理的确立与实施。
具体地说,自觉的生态哲学,必须是具有如下逻辑贯通性的三大认识体系的密切组合:
(一)人与世界任何一个方面的构成,从本质上说都是不能具有无限自由的。它们有机地共轭在一个超越于其上的综合生命体之中。这个生命体的横向与纵向的关系结构都具有超然的独立构成性,包括结构逻辑的必然性和结构衍化的综合制约性;结构互动是这个综台生命体自由展示自身多样性的唯一可行方式,但这种理论上的多样性自由却有不同的发展命运:由于生命的固有本能是其自组织的协调性和有限结构阈内的自修复性,所以,在其结构阈内结构的自由发展会呈现秩序的收敛性,也就是所谓的可持续的生态平衡;而在结构的自由发展超出了安全的结构阈之外时,结构的未来发展将呈现不可预知和不可修复的秩序发散性。这就是生态的病态发展或生态危机。而我们所说的脆弱的生物圈正是这种超级生命的现实形态。
(二)这种生态哲学的前设对人类的特定要义是,绝对的自由是人类荒唐的执著。但“共轭”并不是自由的囚禁枷锁,它的要义是为生态圈内的诸构成提供轨道内的自由和轨道外的限止,也就是说在有限的自由度内生命向自由开故,而在自由度外向自由设禁。闯入自由的禁区就意味着逼迫生态的结构偏离到安全阈之外,用中国人常用的话说就是“伤天害理”。但“共轭”意味着生命有其复杂的“纠缠”机制,对每一个有限自由的构成,它同时表现为面对自身的“存在性”和面对生命的“功能性”。换言之,在生态哲学的语境当中,任何一种所言之物,都应该在指谓和定义的意义上由两相构成:存在性和功能性。前者面向事实的说明并指向其自身,后者面向价值性并指向生命(生态)。这种“一物两谓”是西方现有哲学所阙如的,但对生态哲学的理论展开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与“一物两谓”相应,说理模式也应该是“两行”的,即存在性分析有存在性一行的道理,生态价值性的分析有生态一行的道理。这两种道理的谐一构成生态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内容,包括生态圈的自组织机理和再生修复机理及其生态圈中诸构成的行为方式对它们的意义。
(三)生态文明的人的价值构建和伦理抉择。按前两行的生态哲学认识自觉,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是:本质上并不自由的人类在生态圈的“天理”所赋予的有限自由度之内如何实现自身的精神自由和价值展现的行为伦理?这一问题所标示的深刻要义在于:定义自己是自由的并借助人文系统的构筑展示人类中心论的自由,这并不是一种璀璨的精神文明和高尚的人文世界。人类向自身的聪明才智发起的真正极限性挑战在于,不自由前提下精神自由的弘扬与负责任地“营卫天理”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和谐关系?
四、历史上的生态哲学
如果我们将前一节阐明的“自觉的生态哲学”认识观也理解为一把尺子,并用这把尺子裁量历史上的生态哲学,即把生态哲学的成熟化理解为子母生命之间的共轭共生关系,则我们不得不再次惊奇地“发现性反思”到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是与成熟的生态哲学主题等价同构的。
这个论断的证明也许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论断并不是只言片语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针对几乎全部中国哲学。本文无法完成这种证明,但可以采取一些简洁的方式,从两个方面简约地说明。
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从否的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主流陈述中有没有与前述自觉的生态哲学尺度相悖谬的思想迹象。这需要中国哲学的研究学者集体进行思想搜索。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个人所及的文献没有所说的悖谬倾向。
其二是从正的方面,我们也只能从紧扣所述三大主题的核心角度,给出概要的说明。
(一)关于宇宙本质的认识,中国哲学从巫文化那里承袭来一套复杂而且是层叠着的生命化世界。巫的特质是谋求在不同的生命层面之间自由升降穿梭。周秦之际的理性化思想运动改变了巫祝世界的宇宙模式,但世界的有机性及其天人共轭的基本观念并没有革命性地改变。天人关系仍然有机地“相合”在一起,个体生命的性与命按照“生之谓性”、“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子母生命结构逻辑理性地展开。个体生命是上行生命的子系统与官能载体,同时接受着上行生命系统的命运安排。同时中国哲学是农耕文化中孕育出的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秩序结构认同的哲学,生态的“守信”与作物的丰年、国泰民安、子嗣永续等观念是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天”作为“行健”的超级生命,给予或包容了人类的一切。这是和逻各斯的世界及其基督教“自然为人所设”“人是万物尺度”或者是物理科学将地球仅仅当成物质天体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这使得中国哲学始终不得将“人”以孤立于世界的“主体”姿态与“客体”相对峙,而是谋求“体天道、作天民”的“天人合一”。
(二)天与人的意义是互相发现的。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永恒不变的核心主题,但不论在什么语境的论述之下,言天未尝不言及人,言人未尝不上达于天。而人或包括人在内的天地间诸构成,都同时具有两种不同指向的意义:指向其自身,或仅从与他物相区别的确认意义上的存在性,谓之形而下规定性的“器”﹔而从对天的综合生命系统而言,万物未尝不是对行健之天起到营卫作用的“官”。“器”谓形而“官”言能,这种两行之间“一物两谓”的定义倾向,始终保持于中国哲学甚至中国日常语言之中。“官”完全由上行生命系统或生态系统所规定,“天官失序”是上承于巫文化又具有理性化的哲学觉醒的最大“灾眚”,“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矩”,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天秩天序”。而周秦之际由道家提升而成的最高哲学范畴“道”,也正是从这“天秩天序”当中形而上“脱胎”而出。“有道”“无道”、“中道”“不中道”观念,显然有着对“天秩天序”顺逆合违观念遗存。这样,个体生命就兼具了事实与价值双重属性:人的存在于自身存在的一行论,是“从心所欲”的自由载体;于高级生命官能的“道”的一行论,是“不逾矩”的中庸“天民”﹔对上行“天道”的规矩,“顺之则昌,逆之则凶”。违背生态伦理,殃及自身——这是《易》和《内经》的共通逻辑。个体生命的与天共轭:这里的天是生态系统,它之于人的意义既有综合的“休于天钧”的“道”的规定性,又有《内经》诸大论的显示功能规定性。前者的结构逻辑在庄子的论述中有极其严格的论述,可称之为“两行论”,笔者将对此另撰文说明,此不赘述;后者是“应象论”,这是《内经》诸大传的核心主题。至于生命体之于种系的共轭,则是天人关系在人文系统当中的同构展示:儒家伦理从血缘伦理中出。血缘伦理的核心事实是种系认同,它的内涵是个体生命从属于血缘伦理共同体的母生命系统——血缘伦理是生态伦理具观化,从属于生态伦理。在儒家,唯有将血缘伦理共命运化,生态伦理的天秩天序方能体现于社会伦理的纲常有序。生命体与生境之间的关系,可描述为生命为与生境互动而存在。这应于种种形态的选择进化论——包括拉兹洛俱乐部谋求的广义进化论。但《内经》所进行的哲学假设,完全在生命与生境互动的“根目录”上。为此,“子生命”之于“母生命”,其分类非营即卫——《营卫生会》的哲学意旨不仅限于《内经》所言人体生命,之于任何生命化的组织,营卫是基本的“上行”官能的概括。这些认识,都是在生态哲学的“子母生命系统”共轭互动关系下及其营卫太和的价值设定下形成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生命医学,是这种哲学的忠实践履者和细致结构的探索发现者。
(三)生态哲学的元认识是置人类于非自由的天人共轭的论域之中。这就派生出自然的观念、必然的观念、当然的观念、应然的观念和本然的观念的学理细分。这正是中国哲学深入主题的精深所在。自然的观念当然是指不受扰动的天地宇宙的观念,这在中西方的认识中是有共识的。所不同的是,西方的自然是纯粹物质存在的世界或上帝按原则创造并控制着的世界,而中国哲学的自然是自组织的生命世界,或就是生态圈的自适应自修复世界。所谓反朴自然或者法自然,都是基于逻辑上的对自组织神奇能力的尊重和赞誉。所谓“赞天地之化育”此之谓也﹔必然的观念是逻辑的观念,在结构逻辑的框架下,它指的是诸多有限自由的构成对“共轭”的不可逃逸性,或者现实性地指向结构衍化的命运归宿。中国哲学的必然超越但包涵亚氏逻辑的必然,它不基于因果逻辑而基于结构逻辑,所谓“阴长阳消”是非因果逻辑但是结构逻辑的;当然的观念是有限自由选择论域下的最佳价值判断观念,是针对人的价值选择而言的。譬如西方哲学视“自由”或“天赋人权”为当然,但中国哲学的当然基于“理所当然”,“理”是有限自由的天道限止,也就是天秩天序为人所预置的“规矩”。在道理所容的前提下或被上行规矩所限的个体命运谓之当然;当然之时应对必然之选择谓之应然。应然是从事实性选择到价值性规范的贯通和统一,“从天理,灭人欲”是将事实之当然之道与价值选择应然之理共轭一处的价值体系。从这一点看,当代生态伦理并未出其右;应然的选择如果在自身价值体现上做到了“人与天地参”,即获得了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但同时在效果上有“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人类价值上最高实现的“宜”。“宜”的哲学化价值体现的是“义”,“义理同一”的关系引申出道义,便是中国哲学价值圭臬的不二选择。明白这一点,方能理解宋明儒在天理人欲面前的良苦用心,方能理解“义理”的真正含义。人将有限自由限止下的精神自由发挥极致,并能从心所欲地“体天道、作天民”“与天地相参”,这正是“极高明道中庸”的天人合一境界。或者说,中国哲学在“人”之上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天理负担,甚至丧失完全与世界对峙的“主体”地位,非他,使生态哲学的元观念从未丧失之故﹔人如果在存在与价值选择的两方面具有“良知良能”,能够与义理同一,则天人之间共处的“事实—价值”世界综合体,便是中国哲学谋求的最高境界——本然境界(祁洞之,2007).
拉兹洛的俱乐部对经典物理学的解释系统发出革命性的挑战,几近对“巫性”超验感应给予正面“科学解释”。这是生态及生命认识论的殊可注意的动向,其正面意义不容诋毁。的确,生态哲学或生命哲学的成熟必然要超出经典物理学的解释篱藩,这是生态哲学家及生命哲学家对于尚处于幼稚学科阶段的生态学及生命科学的元哲学功能和善意建议权的行使。但在中国的春秋战国之际,“巫性”被“理性”所容纳的历史或是生命科学可以借鉴的历史珍存:毕竟,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神秘的超理性官能性能否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理论化的处置。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医学可能是不自量地承担了这一点,《内经》极尽了解释之能事“天人感应”和“人副天数”的痕迹当然历历可见。但有两点史家必须切记:第一,《内经》是“古之道术”集成改造的结果,不是汉人的臆想之论﹔第二,它很好地把功能落实到了实处使“营卫生会”与“脏腑”“经络”“腧穴”“九窍”“百官”等功能载体合论一处。其巨大的解释性不断接受临床的苛刻检验得以传世和完善,虽这是中国文化封闭范畴之内的事,但其思想史价值不可小觑。
生物与生境的互动交换方式:这是中国哲学的老问题,也是生态哲学的基础问题。生物圈是诸多脆弱条件的巧妙共轭,每一种上下行或同行间的所与所取都被“规制”在生态法则之内。问题是,这些法则的细致规定性是以怎样的载体和怎样的功能共轭一处的?这是生态哲学最为切要的。“脏腑”“经络”“腧穴”“九窍”“百官”等实存于人体中但生命功能于生命的“生命机缄”和内外交互方式能够被生态哲学家接受吗?目前西方文化熏陶下的生命科学家尚不接受这一点。这是属于科学宗教的问题呢还是属于生命哲学的幼稚的问题呢?但有一点,当代的生命科学和生态科学不屑于对此进行意义探究,则是不幸的事实。
生态哲学将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考归诸于人类伦理意义上的宗教,而对于有两千年思考的真正生命哲学和生命科学实践的历史归诸荒唐的宗教而弃置,这就是我所看到的生态哲学的现状。当然,中国哲学家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立性或许在生态哲学的论域下得到心平气和的对待。如果将地球生命的考察能够获得《内经》对生命体考察的精密程度,那么生态哲学则能够从危机的羁绊中脱身而出,将对地球生命的诊断系统与人类行为的应然系统统一起来,共建和谐生态家园的人类久业。
应当指出,将生态灾难归咎于技术是感情用事的。技术永远是中性的,用于攫取地球资源,可以变为“忤逆”﹔用于保护资源,可以成就“孝子”。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关系,不能够简单地划分为“忤逆”与“孝子”,能而不为与为而不能永远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工业文明伤害了大地母亲,但工业文明的要素并没有罪过,罪过仅仅在于无知。工业文明哺育出的技术,不是也清晰化了大气云图、海洋洋流、海路信风走向、极地构成原理、宇宙风作用原理、磁力线分布及变化路径,以及湿地作用、鸟禽候栖、大陆板块结构互动、地幔地表作用原理等地球生命的原理图景?生态哲学的要务,一是与地球生命学家一道尽快了解地球生命,建立地球生态及生物圈的诊疗养生体系(这是作天民的理论依据),二是建立人类行为的生态后果评估,脚踏实地地为生态立法,三是以生态家园和谐为自觉的人生意义与伦理结构的建立,四是建立两行工业文明及生活方式的制度体系。总之,两百年的工业文明造就当代社会和生态危机是一个基本事实,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地球疾病的性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但疾病所入为诊疗之理。与盲目无知的孪生相伴是:为保护生态而实施的行为导致生态灾难,在我们的现阶段历史之中也并非无稽之谈,所谓“病急乱投医”是当下生态哲学最该避免的一个大忌。
参考文献: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拉兹洛《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祁洞之《本然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
——摘自《两行逻辑论初稿》,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