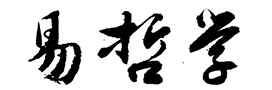我们对两行论的理论关切,始自于对中国周秦文献的体系化处理。我们的理论定位是,中国哲学的发生学源头与“礼乐文明”的发生、发展与崩毁过程紧密相关。首先,从溯源的历史角度,以孔老为代表的春秋时代哲学,其理论基态便可统一定性为:以自身所及的知识积淀为礼崩乐坏的社会病体诊断病因进而提供扶正祛邪的药方。而他们共性的知识积淀又是源于目标统一但理解不同的“古之道术”。这一所谓“古之道术”恰好是积淀于原始的巫文化,并在殷周之际的祛巫化革命中涅槃而出的、旨在为“礼乐文明”提供理论支撑的元理论体系,且该元理论体系其实就是所谓“易理”。其次,从礼乐文明产生的历史源头看,夏商周三代宗教的历史发展逐步形成“宗教文化共同体”观念,并以“人类共同体”的姿态将“天人关系”的逻辑内涵稳定在“生命化宇宙共同体”与“文化人类共同体”的关系之上。与此同时,农耕生产方式逐渐替代渔猎生产方式,并在殷周之际经过周人的制度擘画,成为社会全员共同参与的社会化统一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共同体文化的思想变革促成真正的两行社会:着眼于(人类)共同体体系建设即现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建设的上行社会,以及以直接的井田劳作为代表的着眼于个体利益关怀的生产力构成,即“基础结构”的下行社会。两行社会的现实直接呼唤一种体系化的理论,让两行社会持续地健康和谐发展而不是进入病态循环进而崩溃。“礼乐崩坏”的现实历史发展表明,礼乐社会的病由还是发生于两行关系之间。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周人做的相关努力是,逻辑澄明地理论展现“两行社会”的成物之理、两行关系之理。承继下巫文化的卜筮表达形式即卦爻形式,但在经辞设计上完全体现周人对两行社会关切的《周易》正是这种理论体系化的尝试:六爻中的所谓上下两卦分别代表上行社会与下行社会,而一般事物(卦)的成物之理和两行关系则在“乾坤并建”和“两行并建”的总纲下次序展开,描绘了一幅旨在将任何两行命运体的衍化可能完备地排列于其中的谱系结构。《周易两行营卫论》就是以这种理路,通过对《周易》进行“两行营卫注”的最原始学术探究方式,再现周人的“两行论”哲学。第三,中国哲学的发展,始自于对“礼乐文明”及其背后“古之道术”的综合反思。“命运体-共命运体”关系问题一直是先秦哲学乃至于后世哲学关注的最本质的基本问题。“两行论”始自于对“礼乐文明”的现实关切,但却获得了远远超出礼乐文明的一般化哲学提升。“阴阳”“太极”论便是中国哲学将“两行论”上升到一切哲学前提的基础地位一般理论形态。
一般而言,“两行论”哲学道路的开辟,沿着两个大的方向:其一是“两行系统论”,其二是“两行逻辑论”。在中国哲学论域内,这也是“古之道术”的两个延伸方向。诸子中如《管子》、《孔子》、《荀子》、《韩非子》的哲学,不离于“礼乐社会”或两行结构的一般社会,是在“原旨主义”“两行系统论”层面上开辟哲学;而《老子》、《庄子》却旨在于“古之道术”的“道体”之内进行超越论的、天钧论的“两行之辨”,“两行逻辑论”的色彩渐浓,至于王弼以“得忘论”阐易理,则具有现代标准意义上的“两行逻辑论”的意味,即以现象学意义上“意向性”的变换视域,理解意义化的逻辑内涵。至于邹衍以阴阳衍天地、董子以“人副天数”阐释“大一统”、孟喜京房以纳甲、纳五行方式阐易变、邵雍以“皇极经世”说易理,《内经》以营卫血气通贯人体生理系统,则在“反复殷道”意义上开辟新的哲学。《孟子》将本质上是“两行营卫论”的涵养功夫用之于对人性善端、浩然之气的涵养,在“心学”领域别开生面,引导出宋儒关于“天人”“理气”“性理”的两行论延伸。
在现代哲学的意义上,两行论应该有内涵清晰但道路广阔的理论前景。从传统的中西关系上看,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均是“一行论”的,核心标志就是只有一种统一的“成物之理”,终极统一于“上帝”视角下的统一世界。“本体论”“形而上学”就是在“一行系统论”和“一行逻辑论”的纲领下描绘这个统一的世界。“本体论”着眼于“彼岸”“上帝”统一生成次序纲领下的“宇宙系统论”,“形而上学”着眼于绝对固定逻辑视角下、特别是上帝单一视角下完成化了的统一逻辑。
而“两行论”的哲学前提是在复杂的系统中承认有“两行(n行)成物之理”,异质化的不同“成物之理”之间必然建立两行论的理论视域。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承认世界的复杂有机性,间接指向成物之理的多元性。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领域,在“人与社会”这个典型的“命运体-共命运体”关系体中,“对象性的关系”即“两行并建”的关系被深刻地描绘为“对立统一”,并且创造性地置入“实践”的概念,使得“实践”成为“两行并建”的主体和动力。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天人关系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进而人与人群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商品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都被逻辑清晰地纳入到一般的两行关系之下。辩证的对立统一也本质地体现于两行关系上“两行并建”的对立统一。
逻辑的一行论纲领在西方执着而顽强。“形而上学”只是它的特殊历史形态。逻辑一行论的本质属性是不同逻辑视角所获得的逻辑相关项能够被转换、整合为归一化的唯一视角下的相关项统一,直观的形态就是在上帝面前逻辑具有无矛盾的、完成了的完备统一。不同的逻辑视角,譬如处于数学构建中的“构造论”视角形成的逻辑相关项,与终极完成了的“逻辑形而上学”(理想的PM系统)中相应的逻辑相关项一定是可一致性逻辑协调的。哥德尔定理指出这种不协调的绝对存在性。而历史上,这种不可协调的逻辑现象屡屡凸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康德发现了本质是不可“两行协调”的“二律背反”,但包括康德在内的全部一行论思想家和后世的分析主义逻辑学家都将此“个案化”处置,将之与“语义学悖论”齐观,在“逻辑修正主义”(譬如罗素)的道路上继续贯彻一行逻辑论。
正像哥德尔评价的那样,在逻辑问题上发现“元逻辑真谛”的逻辑思想家只有胡塞尔。胡塞尔的逻辑学是现象学的逻辑生成学。“超越的”意向性自由内在地包含逻辑视域的多元化,而它们之间的可逻辑协调是有现象学内在规定的条件的,所生成的“逻辑地平线”是“多元共建”的“内在实践”结果,并且“地平线”不具有逻辑单一性和终极性,它又是朝向更开放逻辑地平线迈进的新的起点。
我们所说的“两行论”,取名于《庄子·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原意是指向道枢的思想境界的超越之路,“两行”是其超越的路基。既包括“两行系统论”又包括“两行逻辑论”。这是由“道”本身的系统论(衍化论)属性和逻辑论属性(成毁是非等意义展开属性)决定的。从“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韩非·解老》)的面向“生活世界”的现实开放性观之,现象学的逻辑域与道的逻辑域略同,因为其共性在于允许不同的逻辑生成者在不同的“成物之理”逻辑地平线下实施“两(多)行并建”。
两行论的哲学道路开辟尚需同志者共同努力。由于其前景的广阔,还现实地由于它能够在哲学思想基因的层面联系起例如中哲与马哲、中哲与现象学等重大哲学领域,能够充当桥梁与渡津的作用,将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